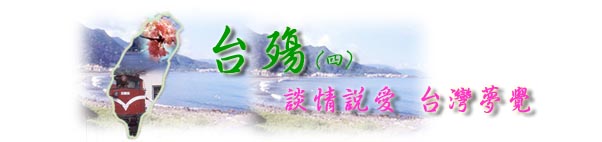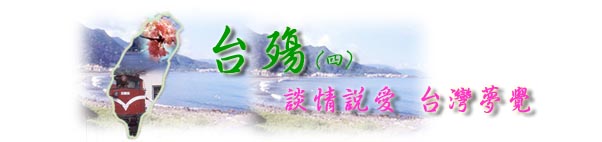他該死 他掀了我的底牌
江南揭露蔣經國傳子不傳賢的計劃
1988.03.25~03.31
民進時代週刊
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經歷了一番波浪繼任國民黨代主席,權力衝突似乎已大致宣告底定,各系統的政治勢力間也已獲致動態的平衡。
這種說法,大謬不然!
國民黨內某些「排蔣」人士已經積極展開水面下的權力轉移計劃,他們的目標是在蔣宋第三代、官邸勢力、情治系統,以及軍力。
近日來喧騰塵上的張憲義離奇出走事件、二二八翻案、孫立人兵變秘辛揭露、乃至於陳啟禮申請再審江南案,都是這次權力運作中的一環,藉由舊案新翻,這些人士想削弱蔣家的殘餘勢力以及頑固的軍方,在七月七日的十三全大會召開前,另立江山。
「排蔣」集團的成員目前雖然縱跨黨、政兩大部門,沒有機會結合在一起,但他們不約而同地在此一方面取得共識,並作出同樣的努力,乃是因為一個極其爆炸性的理由:蔣經國雖然在江南案後的七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講出「不能也不會」安排蔣氏家族出任他的接班人的話,隨後並外放蔣孝武出任新加坡當地辦事院之外交官,但根據蔣經國死後流露出的許多訊息顯示,蔣經國其實自始至尾都沒有真正中斷他的傳子計劃,蔣孝武的接班,實際上要較社會所預料的時間為晚,甚至在他死後。在他生前的許多運作裡,他亦預先佈署了蔣家改革的美譽,外放蔣孝武,是想在民國八十年後,由孝武出面競選總統,接李登輝的班。
蔣孝武官邸罰站三日夜
根據權威人士的說法,蔣經國的接班計劃分為兩大步驟,第一步為由蔣經國總攬朝政,但是派孝武、孝勇深入民問,發展基層。基層的意義,對孝武而言是發展情、特組織中的影響力,對孝勇而言,是藉商務關係結識地方派系及大企業,七十一年的選舉,高雄地方派係的糾紛,孝勇即曾一手擺平。第二步即為進入實質接班情勢的塑造。蔣經國雖然在民國七十年十二月親自提筆將兩兄弟從國民黨十二全大會中央委員的提名名單中劃掉,但是這祇是為恐遭忌的權宜措施,兩兄弟的正式進入黨務系統,舖陳從政資歷,應該是從十二全大以後開始。
兩兄弟中,孝武較具政冶意識,孝勇好大喜功,往往不能權衡情勢,蔣經國雖然都有栽培的計劃,但卻明顯的偏袒孝武,這也是兄弟失和,孝勇搬出大直官邸,常住士林官邸的一個潛在緣由。
蔣孝式的接班態勢,第一步可算是成功了。在江南案發生前,他是國家安全會議一個沒有名份的執行秘書,擔任安全系統與父親間的橋樑,其間,國安會秘書長沈昌煥、汪道淵都將之視為第一助手。這樣的佈局,和蔣介石當年鋪陳蔣經國接班的步子顯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從情、特著手。比較不同的是,蔣經國憑藉親情、政工與調查局勢力,陸續鬥倒了陳誠、孫立人、吳國禎、王世杰、任顯群、林頂立等頭角崢嶸的權力人物,為接班之路舖上一層紅毯,但是蔣孝武卻在剷除了王昇勢力之後,在「江南」案上摔了一大跤。這使得他的接班之路至少得多花個二十年。「江南案」案發後,蔣經國痛心孝武不知珍惜父親為他的安排,曾令四十餘歲的孝武在官邸罰站了三天三夜。
不要說他們是我兄弟!
蔣孝武會急躁地動用軍特力量制裁江南,其合理的推斷應有下列幾種原因:
1.嫡庶之爭。
孝武自慕尼黑政冶學院回台後,在父親的安排下,到退輔會任職,回台後的孝武知道自己另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章孝嚴與章孝慈,他也曉得章家兩兄弟的才幹與學識都在自己之上,同時黨內紅人王昇與章氏兄弟有撫育親情,多次地大力保薦兄弟在黨內參與各項活動,競爭意味頗為強烈,孝慈走入學界,孝嚴卻在外交上大展所長,又得以曾任外交部長蔣彥士為首的洋務派看重,為了杜絕江南晚年寫作蔣傳修訂版及吳國禎傳述及兄弟關係的細節,因此下令殺掉江南。
2.兄弟鬩牆。
孝武從父親那兒獲得權力,孝男卻從老官邸中獲得支持,大直官邸和士林官邸間的爭鬥在宋美齡回國後愈形尖銳。孝武殺掉江南的用意在於向孝勇「示威」,並藉以證明自己在情治單位中的影響力。孝武、孝勇間的「不睦」由來已久,蔣孝武在蔣經國死後,孝勇遲延報訊,使得孝武不能連夜返台,致使兄弟倆曾在官邸吵過一架。兄弟間的「心病」,也是使蔣經國說出「不能也不會」這句話的一個重要原因。
3.根據推論,蔣孝武任職國安會秘行秘書期間,很可能是國、共祕密往來的幕後主要決策者。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可以顯示國、共已獲致任何協議,但是訊息及信件的往來交換卻已是早有的默契,在當年,大同電鍋及聲寶電器於大陸出現,據聞便是「特權」居中接應的結果。蔣孝武早年曾任中央電台(此台專責對大陸廣播,為中央黨部下之一級單位)台長,更是不乏訊息。而江南死前與中共官方有過密切的接觸,蔣孝武很可能是在知悉江南聞知內幕後,殺人滅口。
劉家昌為蔣孝武背黑鍋
4.眾所週知,孝武的生活並不算是很檢點,大陸和台灣間的轉口貿易,似乎都先得到他那兒拜碼頭,在他的身邊也常圍繞著一群影劇圈人士,孝武和大哥孝文一樣嗜近美色,早已不是公開的秘密,數年前的影星谷名倫跳樓自殺事件,據聞就是蔣孝武橫刀奪愛(谷名倫女友為張璐)的結果。後來雖由孝武的密友劉家昌出面頂罪,但顯然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谷名倫事件雖然警方公佈的案情是自殺,但據谷名倫的密友指出,谷名倫是被數名特務從樓上推下來的,至於誰主使,他們有口難言。孝武巧取豪奪的手法,在政界、商界、影藝圈都為人所懼,而江南卻是這方面訊息的確切掌握者,為恐江南寫出這些私德敗壞的事,必先除之而後快。
至於蔣孝武與竹聯及陳啟禮的關係,乃是孝武早年即佈下的籌碼,這層關係奠基於孝武幼年與官邸侍衛的主僕關係,而後發揚於他進入情治系統,掌握國家安全大權之時。
蔣孝武與情治單位的親密關係可從幾個地方看得出來:
其一,江南案爆發後,重要的關係人劉家昌,其姊夫高昇為前官邸侍從武官,和後來成為情報局長的汪希苓曾是前後期同事,高昇雖然沒有參與江南案,但很可能卻是早年幫蔣孝武與劉家昌搭線的人物,而早先劉家昌與陳啟禮合組歐帝威唱片公司,藉著竹聯的兄弟擺平了不少事情,蔣孝武透過汪希苓會找上陳啟禮自有其不凡的淵源,劉家昌為谷名倫事件揹黑鍋,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皇太子吃遍黑白兩道
其二,幾乎所有清冶系統的重要幹部皆出身於官邸,蔣經國這種安排親信出任情治機關的動機,自有其忠貞與安全上的考慮,但也促成了情治人物與孝武長年來的私誼。蔣經國去逝後,到機場迎送孝武的,除了孝勇外,還有郝柏村與國安局長宋心濂,即可微妙透露是項訊息。
其三,孝武浸淫於情治系統中,其權力來源早已不是與職位有直接關聯的政府授權關係,而是其父親早年模塑情治系統所建立的父威,在情治倫理中變成一種主子家百般效忠意識,孝武手握大權往往彰庇人事,悉出己意。譬如前安全局長周中峰對孝武頗有微詞,孝武就用安全局總務處報銷帳目的一點小問題,叫周中峰下台。這種影響力也表現在江南案發,動用情治系統化名一清專案清掃竹聯,一方面儘速將吳敦、董桂森納入掌握,另一方面將周榕、陳功等老竹聯也清除殆盡,以防報復。
孝武與孝勇與黑道的來往,商界與政界都相當瞭解、孝武與竹聯、四海皆有淵源,肇因於中壢事件後奉父命插手選舉與治安,透過早年為「梅花」電影排檔期的關係,和竹聯搭上了線。孝男則是利用幫派份子對不遂其圍標工程的特定人物予以「制裁」,桃園機場的冷氣工程悉由孝勇的中興工程顧問工程公司與中興電機包辦,許多人至今仍耿耿於懷。
兩兄弟皆以世家公子的豪爽與霸氣收攬人心,而以情特力量塑立威嚴。但是在利用過後,即予以辣手清算。
蔣緯國誤赴死亡宴會
江南案以及隨後爆發的十信案,乃是蔣氏兄弟進行接班奪權的一部份,陳啟體與蔡辰洲則都祇是棋局裏的馬前卒,根據民國七十二年前後的國民黨權力結構變局來看,王昇的垮台、孫運璿的中風,蔣彥士打入冷宮,雖然外界揣測這是為李登輝的「蔣、李體制」新班底形成前的舖路工作,但就權力安排的施力點來看,毋寧可看成是為孝武、孝男堅壁清野的綏靖策略,因為上述這些人士雖然彼此不合,但卻都對李登輝沒有太多的恩怨,反而是與孝武、孝勇間有不可化解的矛盾。
江南及十信案發後,蔣孝武雖備受流言指責,但蔣經國至當年八月十六日才對外發佈「蔣家人士繼任總統一事,本人從未有此考慮」的話,這其中的許多調度與安排(包括安排老官邸馬樹禮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原秘書長蔣彥士手下大幅度換血,皆以官邸舊部為主),仍是有利於孝武的,接班的態勢仍是傳統的。至於後來發生蔣氏發表不讓家族人士繼位,並外放新加坡之事,乃是因為蔣經國嗅出孝武對其叔父蔣緯國的鬥爭。
根據消息研判,江南案的目標除了殺死江南,作掉陳啟禮外,孝武還想把蔣緯國也拖下來。
江南刺殺行動前的二個半月,也就是七十三年七月下旬,孝武透過白景瑞等影界人士的介紹,在白景瑞家宴請影星張美倫及陳啟禮等人,汪希苓等人也坐陪,蒞臨會場的另一貴賓則是蔣緯國。蔣緯國事先並不知情宴會內容與一件行刺案有關,江南案發,抽絲剝繭,赫然發現該飯局乃是政冶鬥爭的先聲,「陳啟禮震撼」一書明文指出該天宴會有蔣緯國參加,但卻沒有寫出將孝武,固然陳啟禮有其政治考慮,但也可看出,孝武確實拉蔣緯國參加了這場死亡宴會,江南案發生後這場宴會的消息被封鎖,蔣經國也知道蔣緯國的尷尬,權宜的措施便是外放孝武。
外放孝武,推動改革,讓李登輝逐步培養接班,都是為孝武培養他死後實質接班的條件,蔣經國雖然看不到兒子順利繼位,但總得為兒子留下一片江山,讓國人在緬懷他的同時,也能記得他的兒子。
舊案重翻,瓦解蔣家班
由於孝武的從政資歷不夠完整,未來勢必無法在黨內高人的環伺下脫穎而出,孝武能出任領導人的時機,也勢必要在一個公平競爭、數人頭的環境下才有可能,蔣經國晚年推動改革,一方面為蔣家博得美名,另一方面則為兒子的競爭打下基礎。在為兒子的作為上,蔣經國顯然已盡心盡力,極盡曲折,就他的心情而言,孝武能否克竟全功,祇能靠孝武自己的造化了。
國民黨內「反蔣人士」的集團在蔣經國死後的這段期間內,即不約而同地在各個層面展開運作,首先是於一月廿七日撲滅了孝勇與孔令侃、宋美齡的干政計劃,其次則是陸續地重掀舊案,特別是蔣家當年作為權力鬥爭祭禮的孫立人案與江南案,藉著內幕及新聞的炒作,徹底斬斷孝武憑藉軍特回台重整舊部的希望。
比較微妙的是,這些訊息的流露顯示出「反蔣人士」經過相當細密的佈署,二二八楊亮功報告案、孫立人兵變、張學良幽禁案、以及張憲義神秘失蹤案,都在報禁解除後,特快新聞的各報中獲得默許的炒作。但是,情治系統的佈建卻相對地發出新聞的導誤訊息,譬如張憲義案的案子被導向「反美」的焦點,頗令「反蔣集團」中屬絕大部分的留美派相當尷尬,報禁開放後,新聞媒體已明顯地作為政治勢力的另一交鋒場所。事實上,在十三全大會前的第二波權力爭鬥中,各種蔣經國死前所不容許的權力運作已然舖展開來,山雨欲來之前,狂風早已滿樓,這種情形宛如蔣經國在一九六0年代接班前夕的風雲變局。這場戰爭勢必殘酷,因為沒有人能夠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