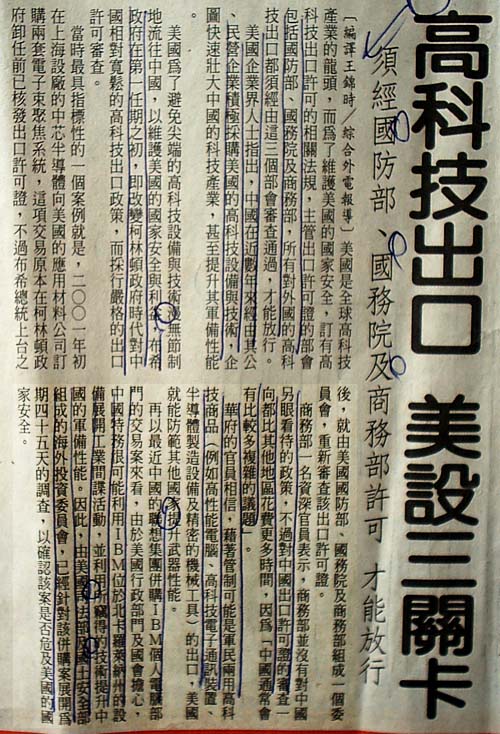|
2005.02.21
|
|
黃天麟:聯電案 政府也要負責
|
2005.02.21自由時報
記者鄭琪芳╱專訪
檢調單位偵辦聯電背信案引發各界討論,國策顧問黃天麟昨日表示,聯電如果真的違法投資和艦,當然要接受法律制裁,但過去中芯及宏力半導體陸續在中國設廠,政府卻視而不見,聯電等公司當然覺得不去會吃虧,因此,整起事件,政府也要負很大的責任,過去政府只會積極開放,根本未有效管理。
黃天麟指出,聯電案顯示政府沒有徹底執行相關法令,一九九九年,張汝京到中國籌備中芯半導體的消息就開始見諸媒體,二○○○年正式浮上檯面,當時張汝京拿的還是台灣護照,錢也是從台灣過去的,還從台灣帶走了許多高科技人才,政府卻沒有任何動作,王文洋的宏力半導體也是同樣的情況,當時政府都說查無實據,其實根本沒去查。
黃天麟表示,中芯及宏力事件讓聯電等業者覺得「守法者吃虧」,當然會想要跟著去投資。黃天麟認為,由於不少相關法律政府都不執行,因此,除晶圓廠之外,過去很多尚未開放至中國投資的高科技產業,也都偷跑過去了。
黃天麟憂心地說,政府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夠,才會對高科技產業違法到中國投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相較之下,美國這麼強大的國家,卻對國家安全相當敏感,中國聯想集團購買IBM PC部門,美國政府就馬上介入調查是否危及國家安全。
此外,中芯想要向美國應用材料公司購買晶圓廠設備,美國輸出入銀行卻不願意提供融資保證,雖然應用材料公司表示「美國公司不賣,日本也會賣,白白損失商機」,但美國輸出入銀行仍然拒絕提供融資保證,理由是「商機是商機,但國家安全更重要」。事實上,美國不賣晶圓廠設備給中芯,日本也不會賣,因為日本也相當重視國家安全。
因此,黃天麟強調,為了國家安全,政府「該說NO的時候,還是要說」,不能商人說會損失商機,就全部放行,更何況,有時並不是真的會損失商機。
黃天麟說,很多產業想要去中國,理由是那邊的市場大,不能喪失商機,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在媒體上的聲明也是這樣說,但根據檢調單位調查,和艦的許多訂單是從台灣轉過去的,並不是和艦在中國拿到的,像這樣的轉單行為,會讓台灣的產業逐漸被掏空、被邊陲化。
因此,他表示,政府一定要「有效管理」,現在幾乎所有產業都已經開放,只剩下十二吋晶圓、封裝測試及TFT等少數產業未開放,既然政府已積極開放,就該有效管理,該執行的法律就要執行,該修法、該立法的,就要趕快修法、立法,像科技保護法就應盡快立法。
2005.02.21自由時報
謝志偉
除了「中元普渡」外,傳說我們還曾有個「台灣普慶」,聽過嗎?
傳說是這樣的。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後,接下來直至一九八○年代,蔣介石(1887-1975)和蔣經國(1909-1988)父子的中國國民黨在全台各地以「清鄉、綏靖、抓匪諜到打台獨」為名,地域不分南北,人民不分省籍,殺的殺,關的關,死傷無數。其間有一天,年漸老,體漸衰的蔣介石為了想知道還能活多久,就召了一個名聞遐邇的算命仙進府來問。算命仙不假思索地回道:「報告總統,不瞞您說,您將會死在『台灣普慶節』的那天」。老蔣緊張地問:「『台灣普慶節』?那是什麼時候?」算命仙說:「報告總統,不瞞您說,還不知道。」老蔣神色不悅地說:「還不知道?那你怎麼知道,我會死在台灣普慶節那一天?」算命仙:「報告總統,不瞞您說,因為,不管是哪一天,您死的那天就是『台灣普慶節』」。
那個算命仙的下場?不瞞您說,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年頭,有多少人就這麼不見了,敢說出心裡話的人,通常是一上場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何況,軍警情特加抓耙仔,滴水不漏,即便是傳說裡編出來的人物也照樣沒保障的。那,還會有台灣普慶節嗎?不瞞您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不管是哪一天,中國國民黨……。
「傳說」者,「傳來傳去大家說」也。「傳說」當然並不僅止於「政治」層面,但是在獨裁政權的時代裡,有關政治人物的「傳說」卻扮演著很特殊的角色。它可算是野史的一種,不具權威感,也無可信度可言,但卻常是被壓迫者宣洩不滿、恐懼和表達期盼、願望的重要管道之一。從而,越是狠毒、強悍的獨裁者越容易、越適合成為政治傳說裡的主角,因為那是被迫害者唯一能排遣他們「無力感」的最有力工具。在戒嚴時代裡,台獨實踐者「江蓋世」的英文拼音因與獨夫「蔣介石」雷同而生的各類傳說就是一例。然而,傳說並不必然隨著「極權統治」的消逝而絕跡。尤其當「極權統治者」的「業績」並未因民主時代的到來而被重新定位時,「傳說」依舊有其必要。我不能不說,除了「必要」外,這更是一種遺憾。
從受迫害者的角度所編出來的「傳說」毋寧是某種程度的「日記」,是一種隨著受迫害者一同被擠壓而變形的「口述之日記」,它的昇華形式則是「筆撰之文學」。而迫害者的「日記」其實則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傳說」,是當權者展現「無所不能」的另一個場域,是獨裁者化腐朽為神奇、「瞞著您說」的最有力工具。獨裁者在日記裡所寫下來的,往往非純「客觀事實」的陳述,而是「主觀意願」的記載。李筱峰教授在其近著《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頁64-70)裡為我們準備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蔣介石來台灣視察一個星期。彼時,由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腐敗、無能和顢頇,台灣人民對「祖國」政府及軍隊的不滿早已達到沸騰的狀態。就於蔣介石在台期間,林茂生主持的「民報」曾乘機提出懇切的「訴願」:
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
然而,在那一個星期裡,遊山玩水和到處接受人民夾道歡迎的蔣介石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寫的卻是:「台灣尚未被共黨份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余此次巡視台灣,在政治上對台灣民眾之心理影響必大也。」眾所皆知,豈止是「心理影響」而已,還有「生命影響」哩!四個月後,二二八事件爆發,林茂生正是諸多死難的菁英之一!
再看十月三十一日,針對台灣行,蔣介石又在日記裡寫道:「巡視台灣之收穫,較諸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民心之所向」早已變成「信心之死巷」,可獨裁者還沾沾自喜於「巡視之豐收」,獨裁者的「日記」之不可信,可見一斑。獨裁者的「日記」不可信,那麼,獨裁者去世後,例如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走掉的那個月,聯合報集團的聯經出版社所出的《仁者畫像 │總統 蔣公紀念文集》裡所收的各種社論、專文可信嗎?隔年的四月,例如台北市立金華女子國民中學「恭印」的《總統 蔣公逝世週年紀念文集》裡面,從校長到老師,從國一到國三的學生所寫的紀念文、哀悼文可信嗎?我們不必浪費筆墨從中舉例,也不必細究那些撰文者的「噁心」是「苦心」抑或是「交心」,畢竟走了的只是獨裁者,而非獨裁體制│ 老子走了,兒子還在呢!更何況幾十年的愚民教育及擾民管制所產生的影響和壓力!
那些逝世紀念文集、報刊社論、各界專文的哀戚肉麻話語若所言皆真,那「中華民國的偉大領袖,中華民族的偉大救星,人類維護正義自由的偉大鬥士」,如聯合報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的社論之開頭語所稱,竟然敢撒手人寰,棄世界、中國、台灣萬千子民於不顧,不就簡直是「該死」了?那種由孝子蔣經國以降,舉國皆披麻,上下全帶孝的場景及話語當然也就跟獨裁者的日記一樣,是在一種特殊的人工環境之下所炮製出來的,是一種主觀的片面意願以包山包海的方式強加在台灣上空所造成的假象,無庸置疑,是禁不起時代的考驗的。那麼,禁得起時間和空間考驗的真話在哪裡?在傳說裡,在文學裡。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蔣介石去世四個月不到,本名林文德的作家東方白寫成他的短篇小說〈孝子〉,由於在台找不到可發表的園地,最後勉強於同年十月登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孝子〉的主角姓黃,家住宜蘭,名已不可考,鄉人只叫他「孝子」。而「孝子」也真是個孝子,不管他那名為黃發的父親生活如何荒唐,聲名如何狼藉,年輕時吃喝嫖賭,年老時與藥為伍,孝子總是只說他的好話,且「把他父親想成是村裡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年,老弱多病的父親終於走了,孝子花了大錢遠至萬華買了福州杉棺木,又找了萬華最有名的風水師上山找了個龍穴。至於墓碑,則特地派人到花蓮的太魯閣採購了一塊大理石墓碑,然後再從台南聘請了最有名的刻碑師傅來,準備在墓碑上刻上最體面的墓誌銘。然而問題來了,墓誌銘要寫什麼?身為百萬富翁的孝子就包了一個大紅包請來宜蘭當時唯一的秀才為他父親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墓誌銘。只是,儘管秀才絞盡腦汁,無中生有地寫出來的內容,孝子讀了後,還是覺得不滿意。最後,他決定自己帶著紙筆上山到各墓地去抄人家的墓誌銘,看到好的就記下來,準備回去後再重新組合,湊成一篇盡善盡美的墓誌銘給他父親。
這一天,又上山抄墓誌銘的孝子累到睡倒在一塊墓碑旁。醒來時,天已全黑,張開眼,卻看到每塊墓碑前都跪著個穿白衣的男人或女人,而且每個人手裡都抓著塊石頭,披頭散髮地在努力磨掉墓碑上的墓誌銘。偶爾還有一個牛頭,一個馬面手拿叉戟,來回巡邏,監視著那些男女。孝子好不容易克服了心裡的恐懼,就近問一位工作中的老伯說:「阿…伯…你們三更半夜在這墳場磨這墓碑做什麼?」老伯一邊繼續磨墓碑,一邊說:「少年家,別來打擾我!我必須在天亮雞啼前把這些字磨光,否則回到陰間,閻羅王又要給我更多的刑罰」。
在孝子的追問下,滿頭大汗的老伯才接著說:「這還不是我的兒子害了我!假如不是他在我的墓碑上刻了這許多胡說八道不合事實的墓誌銘,我今天也不至於落到這步田地。」原來,閻羅王命他們晚上來「洗刷」他們「不該得的虛名」,結果,「那些沒有墓誌銘的,晚上可以好好睡覺」,而他們「這些有墓誌銘的,晚上就被牛頭馬面牽來這裡磨自己的墓誌銘……如果磨光了便完事也好,可是,天一亮,這些磨光的字可又顯出來了,於是第二天晚上又得開始磨。啊!這苦日子不知哪一天才能完結,要不是我兒子害了我,我也不會死了還受這麼大的罪。」
孝子靜靜地聽著,老伯又說:「唉!這些死人的兒子也未免太傻了,他們以為一旦為他們父親刻了漂亮的墓誌銘,便能蒙騙別人了,閻羅王手裡的鬼錄記著我們在世時的一言一行……再說騙騙活人嗎?你想哪一個活人看了這墓誌銘會相信上面說的鬼話?」話說完沒多久,天已微亮,已有雞啼報曉,磨石聲漸歇,牛頭馬面帶著眾鬼紛紛離去。孝子茫茫然地下了山。不幾天,孝子父親墳上的大理石墓碑已豎好。村人看了都大失所望,原來,墓碑上除了死者的名字和生死年月日以外,竟沒半個字的墓誌銘!從此以後,沒人再叫「孝子」為「孝子」了。孝子直到臨終前,才告訴他的子孫實情為何。
東方白的寓言作品在台灣文學家裡是有名的,這篇短短沒幾頁的小說除了很巧妙地應用了希臘神話「西西弗斯」裡的母題外,放在蔣介石去世那一年,台灣處處滿佈著「墓誌銘」的歷史氛圍來讀,更有隱喻之妙。一時間,我們不由要問,到底是誰在「鬼話連篇」?死者「黃發」隱指「謊話」,好個東方白,深知台灣當時之既黑!
回到眼前,日前報載,蔣方智怡女士已代表蔣家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簽約,將兩蔣日記交之保管五十年,並稱兩蔣日記是屬於中國人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國的土地上。日記原本在台灣,如今說,希望日後回到中國的土地上去,倒是清清楚楚地證實了,在他等的心目中,儘管「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要說起「正統」,那對不起,中國是中國,台灣連邊都沾不上!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當初無法接受李登輝當中國黨的主席,當「中華民國」的總統之故。這就是為什麼,民進黨執政後,他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抱持著「寧予外人,不給家奴」的態度之故。蔣方智怡甚且當眾明言,擔憂兩蔣日記在台灣會受到不當的「濫用」。我們對蔣方智怡所代表的「蔣方質疑」予以尊重,但是身為台灣人,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的前夕,憶起直到蔣經國時代的林義雄祖孫、陳文成等慘案,我們也有「台方質疑」,那就是:終其兩蔣時代,中國黨「磨掉」公領域的台灣歷史,致其千瘡百孔,今卻獨留╱毒瘤獨裁者私領域的完整日記,不管所載為何,吾人絕對不上「私而忘公」的當!其參考可也,若要求真,還不如回頭翻閱人民的文學!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獨裁日記當符令,鬼話連篇焉能信
帝王閻王無所禁,牛頭馬面算英俊
台灣普天難同慶,生不逢時遇歹運
有碑無文多少命,墓誌悲鳴代拓印
(作者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2005.02.21台灣日報
【給謝揆的建言】(系列一)
新任行政院長謝長廷提出「共生合作」理念,獨台會會長史明老先生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如果自己的立場不清楚不堅定的話,所謂合作會變成「第三路線,可能會因為戰術的改變影響到基本原則。而獨派團體質疑謝不重視正名運動,史明認為,陳總統是中華民國總統,不應該由他來推動正名或獨立運動,他的工作是為獨立進行準備,包括國際認同和國內工作都需要進行體制內改革。有關國民黨王馬黨主席之爭,史明認為,如果王金平不會善用黨內台灣人力量,終究贏不了馬英九。
戰術運用要配合原則
史明對謝長廷共生合作理念認為,戰術的運用要配合原則,如果影響原則就很不好。過去留學生可以出國都要有國民黨關係才出得去,不過有些留在國民黨,有些就出來,如許世楷等人。過去出國留學生有80%都是理工科,讀的書缺乏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更不用說哲學、歷史等訓練。那時候罵國民黨就是獨立,敢罵國民黨就以為在推動獨立,這是感情獨立。
史明強調,政治上講善意只是觀念,但政治是講現實、政策,說完善意之後要怎麼做才重要。如果說善意是「投降」、「退一步」的話,那就不行了。講「非零和」是戰術性的操作,缺乏戰略和原則。謝長廷也是律師出身,雖然比較靈活,但如果沒有認識論理學的基礎,就會沒有尺寸,尺寸多長不會量,沒尺寸就用猜的。就像要殺魚,沒有刀路,刀拿起來就要砍下去,這樣不行。
共生會脫離台獨路線
史明指出,共生觀念是日本京都大學一位教授提出來的,但這已經是個舊觀念了。謝揆的「共生」是變成「第三路線」,完全脫離台灣人獨立的路線。甲路線要和乙路線合作之前,自己立場要堅定,才能從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出發,如果戰術上有必要合作才需要合作。但如果自己的路線理論基礎很弱的話,說要和乙路線合作,可能讓戰術改變原則。過去阿扁這點可以說是失敗了。
史明進一步闡述說,所謂第三路線必須先堅定自身的立場。過去國共鬥爭發展出來第三路線,重慶抗日鬥爭,一邊是重慶的國民黨蔣介石,一邊是延安的毛澤東,兩邊都是獨裁,大家都不要走獨裁路線,後來發展出民主路線。現在兩岸問題,也變成主動權都在中國。善意是不是要投降?如果惦惦沒步數,一個球也沒有丟到中國那邊去是不行的。為什麼不能善用美國去壓迫中國呢?中國丟球來就要丟回去,不能被動。
外交不主動就沒辦法
史明也指出,外交要爭取主動,沒有主動就沒辦法。以前是中國丟球,國民黨接球之前還會有動作。如九二年時中國主動提出「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黨也回應說「一個中國」,但相爭中國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說各話。當時還有討價還價空間。
史明認為,扁政府要和國民黨、親民黨合作、拉來拉去,和共產黨也要如此,但是自己站不穩腳步就會亂掉。台灣人應該怎麼走,這個不清楚不堅定,和人家接獨就變成「第三路線」,獨立的原則就會沒有了。事實上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要合作不可能,1949年前國共有兩次合作經驗,但中國殺很多國民黨人,國民黨也殺很多共產黨人,大家都記在心裡,回去中國是回鄉玩,不是要回去住。現在倒是台灣人對中國幻想比較多。
扁應尋求台灣人合作
有關宋楚瑜問題,史明說,宋楚瑜是自己「後背揹紅金,還要替人看風水」。他有準備要出來(國民黨),2000年因為他出走國民黨,阿扁不可能拿到總統職位。國民黨和親民黨不一樣,國民黨還要黨產,但宋楚瑜省主席累積下來的資本已經雲消霧散。這次立委選舉後他會被淘汰,只會維持到年底縣市長選舉。為了活下去,上次和國民黨合,現在為了生存和民進黨也可以合作。
史明同意,宋楚瑜不會一下子就靠向扁政府,現在作態也只是「拉抬價碼」,只要他要活下去就會不擇手段。他和民進黨合作也有失有得,得的是繼續存活下去。扁讓他有生存空間,這點扁做的並不對。扁認為為了立法院,和親民黨合可以補足立法院的席次,但這是走後路、暗路,不是光明磊落的路。如果要走正路扁獲得台灣人的選票,票不夠是自己的責任,選舉時宋楚瑜也不會把票投給你,必須去找支持你的大眾。民進黨的招牌是獨立,所以應該找台灣人。立法院的問題應該公開讓輿論討論,讓民眾對立法院施壓。如果為了處理現實問題違反原則,反而去找你要革命的對象。
史明強調,獨立運動是平時要做的工作,不是選舉時刻才找民眾,沒選舉就不認識,這樣不對。種瓜就收瓜,種豆就得豆,緊急時才要找民眾就會找不到人。民進黨面臨一個危機,民進黨沒有行政經驗、群眾基礎薄弱,獲勝是偶然不是必然。高層只有少數幾個繞來繞去,這會變成寡頭政治,繼續走下去就變成獨裁,違反民主路線。像正名運動也是,動員一下之後就沒有了,台灣人和民進黨在脫離,執政後更嚴重。
馬比宋有智慧、理念
談及蘇貞昌,史明說,他1993年回台灣後,蘇選屏東縣長時為他站台站了五場,他們都是台大畢業、律師出身,和謝長廷靈活個性,碰到事情就想這樣走那樣走比較好的「拐來拐去」的個性比起來,蘇貞昌比較有「土氣」、「率直」。兩個人個性各有優缺點。但是講到要強化民進黨體質,他也一樣碰到民進黨「獨立牌」如何處理的問題。沒有處理好,也是一樣的情形。
至於,王馬黨主席之爭,史明認為,在政治智慧和手腕上,馬英九比王金平高明。王金平對別人是「這個人有也好、沒有也好」,不會對你這個反對,那個反對。但他不會運用台灣人的特色,他也不敢表現出來去找外省人背書沒有用,連戰也是一樣,連戰沒用就是這樣。馬英九有鐵票,王金平有的話是黨內台灣人的票,如果他不會利用就會輸馬英九的鐵票。但王金平有野心,面前吊一塊肉,要去咬是人的本性,他是否出線還是要看國民黨裡面的台灣人。馬英九很會表現,比宋楚瑜有智慧政治理念,宋只是個野心家。
體制內改革扁擔重任
史明再次強調,扁總統不需要講獨立,中華民國總統打倒中華民國不可能。他的地基、牆壁、一磚一瓦,連柱子屋頂,都是中華民國的,把他拆了就會壓死人,要拆中華民國是體制外的工作,這是角色的問題。但是台灣國際關係和國內體制內改革路線,他的責任重大,包括一、還政於民重視民主;二、台灣國土處理好,不能放空營讓中國情報人員自由來去,甚至連鴉片槍枝走私都進來;三、台灣人要進步,做人要有責任,政府沒責任感,下面的人不會進步;四、提高台灣保衛台灣的意識,不能隨時倚賴中國。 .....2005-02-21【台灣日報】
2005.02.21自由時報